梁实秋夫人
时至今日,已经没人能说清上海滩第一家舞厅开在什么时间、开在哪条弄堂了。但是,不论时间怎样更替,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说到舞厅,上海人总会条件反射似的指向百乐门。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在千年古刹静安寺左近购置地皮建造PARAMOUNT HALL,外观采用美国建筑史上非常前卫的ART DECO建筑风格,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筑设计的时髦宠儿。在确定中文名称时,这位有着超越时代眼光的商人在“派拉蒙”和“百乐门”之间取舍不定,据说是他那位目不识丁的夫人做出了最后决定。
百乐门开业之初,由一个法国人承租经营,他把所有的法郎都用在百乐门的装修装饰上,紫铜的双开大门,一楼大厅悬挂着12米高的水晶吊灯,双廊回旋楼梯镶嵌了法国南特的红木地板,一排排的镀金铜钉沿着回廊延伸到二楼舞厅,映衬出上海名媛编泮鞋的细长高跟。围绕二楼500平米的主厅,周围有6个接受预订的迷你小舞厅,专供达官显贵和名媛公子私人聚会或者婚外偷情。最令沪上名媛喜欢的是阳台上那座小舞池,地板的磨砂玻璃下面安装了当年举世一流的七彩灯光,脚下流光溢彩,如意郎君抱满怀,华年似水,佳期如梦,百乐门的夜夜笙歌是名门闺秀绽放的一代芳华。
赵四小姐的遗憾
1935年12月20日晚上10点钟,两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从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一号开出,穿街过巷迤逦南行,10多分钟后,悄无声息地停在静安寺斜对面百乐门舞厅楼下的阴影里。坐在警卫车里的侍卫长谭海趋前一步打开车门,先出来的是袅袅娜娜的赵四小姐,稍后,少帅张学良也探身出来。门童恭恭敬敬推开紫铜大门,一行人刚踏进大厅,立即传来“上海五大歌后”之一李香兰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心底死水起了波动,虽然那温暖片刻无踪,谁能忘却了失去的梦。”
赵四小姐听着这千娇百媚的歌声,心里浮现的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句,想到自己虽然能和少帅长相厮守,却终究不能堂而皇之嫁给他,听别人喊一声张太太,这不能不说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赵四小姐挽着张学良步入二楼舞厅,金发碧眼的法国大班一个手势,乐队立即停下来,等张学良坐进包厢,这才重续前曲。舞池里的红男绿女只能目送这位“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匪’代总司令”落座,谁让人家既有权又有钱呢。不过,虽然张学良舞技超群,他今天却不是来百乐门陪赵四小姐跳舞的。
半个小时后,趁每晚照例有一曲暗灯舞的机会,张学良在谭海的带领下,迅速来到隔壁包厢,里面只有一个留有髭须的中年男人,见张学良进来,男子把礼帽放在胸口示意,却一句话没说。他就是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员刘鼎,负责为他们秘密联系的人则是张学良的东北同乡、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
百乐门有一个西餐厅,最出名的就是那上海式的西餐。那些随先生出来跳舞的太太们,不能像舞小姐们那样随性而舞,总是会和几个相熟的女朋友一起,去西餐厅里吃上海式西餐。除了“菲力牛排”、“冰封三文鱼”之外,还有“柠檬煎黄鱼”和“红酒煨野鸭”。而这种西餐后来只有在台北的军官俱乐部才能吃到。俄式牛尾汤、餐包、鲔鱼沙拉、煎牛舌、苹果派、夏威夷咖啡,上海式的西餐比较清淡,有点像法式西餐,再来一杯白葡萄酒,姿态优雅地浅酌慢饮,舞台上身着白色旗袍的李香兰正风情万种地唱着《三年》。
不过,作为张少帅的“地上情人”,赵四小姐却无法享受这种悠闲,她只能落寞地待在包厢里静想心事。事实上,在1934至1935年中,赵四小姐在上海停留的时间累计也没有超过半年,百乐门她也只去过三次而已。
和同时代的上海名媛相比,进入百乐门的赵一荻既没有海派文化熏陶过的浪漫,也不具备上海滩新潮女子的开放,三次中的两次她都是孑然一身坐在包厢里当看客,虽然她曾是天津、沈阳、北平三地的舞厅皇后。当然,她只需要这样的惊鸿一现,第二天沪上大报小报都会在头版头条印上她的消息——聪明的赵四小姐,她来百乐门不过利用报纸给远在北平的于凤至传递一个信息——“我在上海,与汉卿在一起”。
古典美人刘淑媛
有了南北名媛的捧场和做秀,百乐门在沪上娱乐圈里的名气扶摇直上,虽然那个时候上海先后有了第第斯、新仙林和大都会三家顶级舞厅,但是都不如百乐门名头响亮。别说数不胜数的“海上选美”颁奖仪式在这里举行,“沪上歌后”评比在这里举行,“电懋影星”比赛在此举行,也别提名噪一时的法兰西交际花珍妮弗在这里一展歌喉,很多躲在深闺多年的名媛也往往在夜深人静时分来到百乐门一展姿容。
1938年12月,连续几天的凌晨2点,一个气质华贵、风华冷艳的少妇准时出现在百乐门的旋梯上,这就是著名的“古典美人”刘淑媛,父亲是浦东数一数二的富绅,1932年嫁给《时报》总编沈能毅。坊间盛传刘淑媛最是标致妩媚,同张爱玲一样,一年四季喜穿旗袍,一口略带浦东土音的吴侬软语,粘粘糯糯又甜甜,摄人魂魄,却一直深藏不露,无人能识。
刘淑媛每次来百乐门总是提前预订灯光舞池,她并不特别热衷跳舞,在舞池里喜欢小女孩似的滑步玩儿,让侍者搬开桌椅板凳,坐在灯光里痴痴的笑。有时候手托香腮,在霓虹闪烁中凭栏远眺,心绪仿佛午夜的白露,一层层落满雕花栏杆——那一年是刘淑媛“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时期,沈能毅在外面偷娶一房姨太太,在外滩金屋藏娇,刘淑媛一腔情爱顿时倾覆到风霜白露之中,她来百乐门也无非是打发一下寂寞空虚的时光。
不过,几次夜行之后,灯光舞池里有了男人的身影,先是江浙军阀卢永祥的公子卢小嘉。不久,卢永祥战败逃往日本,汪伪政权占领上海,卢小嘉也不知所终,刘淑媛的身边换成了汪伪政权的上海市长陈公博。
“上海第一美女”的异国之恋
早在刘淑媛的身影还没有出现在百乐门的1934年上半年,一位俏丽的名媛已在百乐门引起轰动。人称“上海第一美女”的张雅容从美国归来,她的探戈和吉特巴学的是正宗的拉丁风格,在百乐门一亮相,立即惊艳上海滩。
张雅容的父亲是上海电报公司董事长,垄断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电报业务,张雅容本人身材高挑,肤如秋后茭白,白皙可人,追求者不绝于道。由于在美多年,张雅容英语流利,喜欢与洋人交际,是百乐门里罕有的“里外手”,华人洋人全都吃得通。
刚开始张雅容也喜欢包下灯光舞池,但是她的舞伴和各路朋友实在太多,万不得已只好屈尊在大舞池里订下固定座位,每晚轮流起舞,等她这一圈下来,早已是子夜时分,驻唱的歌星都已经换过四五次。由于张雅容的出现,许多轻易不抛头露面的大人物纷纷来到百乐门,诸如汇丰银行的总经理,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的大班,美孚(中国)公司总经理等等,都拜倒在张雅容的石榴裙下。
张雅容善饮,百乐门的舞厅大班专门为她特制一酒柜,里面冰着清一色的法国干邑。但是有一天,张雅容桌上突然摆了一瓶意大利“贝里尼”,这种鸡尾酒用意大利山地桃汁加粉红香槟勾兑而成,奶白色的桃汁掺进红色的香槟透着一股子亚平宁半岛特有的颓废颜色。
张雅容叫来侍者,刚要发问,一名风度翩翩的洋人突然站到她面前,用意大利语夹杂英语自我介绍,张雅容这才知道他叫加里亚佐•齐亚诺(Cialeazzo Ciano),身份是意大利驻华公使。事实上,那个时候的齐亚诺刚刚由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升任驻中国公使馆公使,31岁的齐亚诺是个美男子,他之所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只有一个理由——他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女儿爱达的丈夫。
情感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齐亚诺和张雅容的相遇就像一篇意大利童话,只不过童话的地点发生在30年代的旧上海。那天的齐亚诺告诉张雅容:“亚平宁山区盛产白色桃子,夏末初秋正是蜜桃成熟季节。这是我专门从威尼斯那家著名的夏利酒吧(Harry`s Bar)为你带来的顶级‘贝里尼’,我想,今夜我们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没有人记得那夜他们是盘桓在百乐门还是直接去了其它什么地方,反正从那天起张雅容成了齐亚诺的中国情人。已经被选为墨索里尼继承人的齐亚诺亲自允诺张雅容“会让你成为我的妻子”,但是,几个月后,随着齐亚诺匆匆应召回国担任意大利外交大臣,这对异国情侣终于再也没有相见,百乐门华丽的回马廊里空留上海名媛无奈的等候。
1944年1月,齐亚诺在意大利维罗纳监狱以“叛国罪”被墨索里尼下令枪决。从此以后,百乐门再也见不到张雅容的身影。
倾倒众生的“歌星皇后”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歌舞升平背后是短暂的繁华。6月20日华灯初上,来百乐门跳舞听歌的汽车已经在愚园路和梵皇渡路排起了长龙,一个小女孩穿过车辆来到百乐门门前。门童面带不屑地拒绝为她开门,并脸若冷霜地问她有没有预订位子。而在两个月后,这个门童看见“上海市救灾筹募委员会主委”杜月笙亲手给这个小女孩颁发“歌星皇后”荣誉时,羞愧得不敢抬头看。
这个小女孩子就是只有15岁的韩菁清,她父亲是湖北商会会长,在上海经营多家铺号和钱庄,与黑白两道关系都非常融洽。
韩菁清是被请来做压轴演唱的,那一年“上海小姐”的评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韩菁清争夺“歌星皇后”位子的只有“金嗓歌后”吴莺音。吴莺音是百乐门的当家招牌,拥有大量的固定歌迷和支持者,沪上许多名人大亨不遗余力地捧她坐上“歌后”位子。
那天到场的大部分熟客拿到新版曲目单后都大惑不解,为什么吴莺音成了“二牌”?压轴的韩菁清何许人也?在众人的纷扰和怀疑中,韩菁清表现出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冷静和成熟,她没有躲在幕后,而是始终坐在台下边喝橙汁边静静恭听吴小姐的演唱。
等到凌晨2时韩菁清登场小试歌喉,偌大的舞场突然鸦雀无声,一曲《夜来香》唱罢,细细小小的声音小虫一般在听众的耳畔徘徊,是周旋?是胡蝶?还是白露?是又不是,熟悉又陌生,亲切又疏远,似是而非之间,韩菁清已然让众生为之倾倒。果然,到8月20号名单公布之日,杜月笙、吴开先、梅兰芳依次宣布获奖名单:“上海小姐”王蕴梅,“坤伶皇后”言慧珠,“舞星皇后”管敏莉,“歌星皇后”韩菁清!
一年后,王蕴梅、管敏莉相继嫁作他人妇,断然退出娱乐圈,见惯了百乐门的夜夜笙歌,她们深居简出,相夫教子,再未回头。作为梅派传人的言慧珠,风流潇洒不拘小节,一直在百乐门混到上海解放,“文革”中上吊自杀。韩菁清则在1949年去了香港,后定居台湾,以“上海歌后”的头衔游走歌影两界,1975年嫁给“雅舍主人”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者夫人。
后记
岁月已经把旧时代的百乐门远远关在门外,至今仍在人世的上海名媛,恐怕只剩下两位80多岁的老人唐薇红和金妮了。而2002年修葺一新的百乐门,无论站在街口的哪个角度去看,仍然是一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建筑。
“我感觉现在的百乐门就像是铜钿贴出来一样的,虽然贴得跟老早蛮像的,但是总归少脱点啥。阿拉格辰光唱起歌来,台下头的人不是往我身上掼花环,就是送过来一只只飞吻。侬看现在,冷冷清清,根本不可能再有阿拉当年的气氛了。要晓得,百乐门灵光嘛就灵光了各种味道呀。现在有点像游戏,白相相蛮好。今朝阿拉来,看到百乐门就像做了一场梦,梦一醒,啥么事阿没了。”金妮坐在百乐门新装修的舞厅里闭着眼睛回想从前。
可是,从前只能是“斑驳的回忆和苍茫的留恋”,是上海滩的旧时月色,是花园洋房里渲染出的那缕高贵气质,是繁华过后的一角残梦——如果一定要给百乐门找一个比喻,借用《玲珑》里的一句话:“糖似乎很甜了,终不及她;蜜似乎更甜了,仍不及她。那糖和蜜的混合物呢?近乎了,仅近乎了若干份之一……”
——摘自《左岸沧桑,右岸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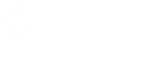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